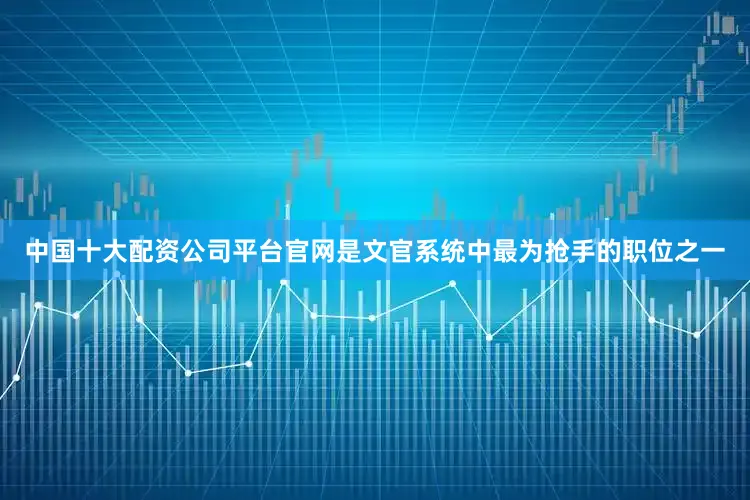
乾嘉时期的三朝名臣吴熊光,在他所著的《伊江笔录》中,曾谈及自己在乾隆年间一段颇为辛酸的仕途经历。
乾隆三十九年,吴熊光因其才干,被提拔为正六品内阁侍读,随后任刑部郎中。在刑部任职期间,他展现了过人的才智,成绩斐然。在一次京察中,他也因此被推荐保送至都察院担任御史(正五品)。当时,刑部尚书阿桂——一位深受乾隆皇帝信任的大学士,十分赏识吴熊光,决定取消其御史任命,转而推荐他担任小京堂(各寺院的主要或副职)。然而,这一转任必须得到吏部的同意。身为首席军机大臣,阿桂在吏部的面前自然有着很大的话语权,吴熊光本应轻松通过。然而,吴熊光却因与当时兼任吏部尚书的和珅关系不佳,坚决拒绝欠和珅一个人情。谁知,吴熊光这一决断却成了他仕途的瓶颈,他的御史之职就这样搁置了整整十几年,直到乾隆晚期,他才终于升任四品小京堂。就这样,一段十余年的光阴白白浪费,正应了那句古话——“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”。
展开剩余73%若细读这段史料,若不留心就难以察觉其中深藏的端倪。然而,从吴熊光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出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:清代都察院的御史地位尴尬且升迁艰难,成为了许多志在高升的官员的无奈选择。
都察院在清代的官制体系中,除了六部外,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机构。它下辖六科、十五道、五城督院、宗室御史处等多个单位。我们重点关注的,是十五道御史这个职务。清朝的十五道是按省区划分的,每个省区根据其事务的轻重,配置了不同数量的御史。每道都有一位掌印监察御史(正四品),满、汉各一人。部分省份的御史数量较多,例如江南道有满汉各三人,而山西道、山东道等地则有满汉各二人。其他省份则仅设掌印御史,不设一般的监察御史。根据《大清会典》的记载,十五道御史的总人数为137人。
需要注意的是,作为御史,他们不仅负责稽核本省的事务,还需负责监察京城中的各大衙门。例如,河南道的御史负责监察内阁、顺天府以及大兴和宛平两京的县事务;山西道的御史则要稽查兵部、翰林院、六科、户部仓场等重要机关。原本在明代,御史的地位颇为高贵,尽管仅为七品小京官,但其职务至关重要,是文官系统中最为抢手的职位之一。
在明代,成为御史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是进士出身,并且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。这是因为御史一职需要对朝廷的文武百官进行监督,甚至监督皇帝,而新科进士往往敢于直言,敢于提出批评,不惧权贵。相比之下,久在官场的老臣或地方知县,往往由于经验和人情的牵绊,难以发挥监督职能。而知县通常也能成为御史,因为他们具有基层治理的经验,对于地方事务更为熟悉,不容易被权臣迷惑。
然而,无论是新科进士还是地方知县,要成为合格的御史,都需要经过一年的“试职”期,这一期间需要掌握律法制度,并通过考核才能正式上岗。
相比于明代集中的皇权,清代的皇权更为集中,尤其是雍正帝实行“科道合一”的改革后,都察院的地位逐渐下降。此时,清代的御史虽然仍是正五品官,但他们往往不是刚刚出任的进士,也不再是地方的基层知县。大多数御史都来自翰林院、内阁或者六部,而这些出身的官员往往更注重其他的升迁路线。对于翰林院的成员而言,转任御史几乎被视为一种“奇耻大辱”。在翰林院看来,最理想的仕途是进入詹师府,成为左右春坊的编修,进一步晋升到内阁担任要职。若是被转为御史,便意味着仕途的瓶颈,几乎注定难有前途。
即便如此,清代御史的职位依旧具有特殊性。一旦任职满期,御史往往会被调往其他道继续担任职务。这种“辗转调动”的做法意味着,御史很难跳出都察院的范围,长期以正五品的身份待在一个低级职位上。而对于那些运气不佳、时运不济的御史来说,他们可能会在这一职位上呆上二十年甚至更久,始终无法得到升迁。
晚清时期的何德刚在《春明梦录》中曾提到:“同光以后,御史多由翰林院编检,或担任各部郎中、员外郎的序补。其实,翰林一等得京察,或积资开坊;部员得京察一等者,亦不愿考取御史。”这表明了当时的官员普遍对御史职务的态度——既不愿担任,也不希望进入这一“升职无望”的岗位。吴熊光的经历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。阿桂之所以要把吴熊光从御史名册上注销,正是因为他深知,成为御史意味着仕途前途渺茫,升迁的机会几乎为零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查查-国家正规炒股平台-配资正规网上股票配资-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